今天,姐姐死了。也许是昨天,我搞不清。
在一切开始时,她问我:“你可以当我的弟弟吗?”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我回答:“哦,我怎么都行,如果你想,我们可以这么做。”
与她共处的日子里,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,甚至越来越糟,因为我一刻不停为自己的冷血和淡然感到羞耻和愧疚,我本该开心并满足的啊。
直到我觉得麻木为止,最后我无感的承认了别人没法从心里升起一丝的感觉。
那天莫名其妙的,我看到4个古怪的穿着全黑西装的人,他们自称是她的家人,古怪的给我塞了一堆东西,并要求我马上举办葬礼并忘了“纸鸢”。
真荒谬,他们连名字都说错了。但,无所谓了...我也不想和他们争。
他们用了一笔小费用给她主持了一场简短的葬礼,它实在太快,而且太简陋了。
我们本该几天后挑个阴雨天穿着黑衣撑着黑伞去给死者下葬的。但他们直接给我套上了一件西装,直接在下葬后进行了这个程序。
他们中我看着像是首脑的那个,他的西装上有一记红色的印记,领带打的随便。我从他身上看出漠不关心,他从没有把头扭向我,哪怕是那些必要的谈话,他也总是交给他身后的那几个人,他总是在看着那个棺材,但哪怕都这样了,他已经摆出怠惰的神色。于是我继续观察,我看到了一个并不严肃的形象,他在和其他的人讨论时,常口吐出俚语和一些不礼貌的词汇。但他看到自己衣服上很细微的绿色污渍时,他摆出了无所谓的态度。
比起首脑,我感觉他更像个自大但不注意自身细节的审计员。
一切结束的太快了,我还没来得及从其他人身上看出什么,这一切就结束了。
我听到他们在默哀时交头接耳,虽然我也走神了,但还是在结束后质问了他们,但他们却不以为然。
等这一切结束后,已经是黄昏了,他们马上就走了。
他们很过分吗?不然。
我注意到了,他们葬礼时,好歹也哭了一场,虽然很假。而我...没什么感觉。
我们下葬时,我昏昏欲睡,甚至在中途突然想到她死因的滑稽而捂住嘴笑了起来,就像我听到了一个人坐敞篷车被子弹击穿头颅的地狱笑话一样。
在默哀时,我把注意力全放在观察那些人身上了,而这也只是种无聊的消遣。
我很疑惑,她的来和她的去,在我来心里看来难道都一样吗?无所谓吧。
这个疑惑伴随着我倒在床上开始掌握剖析后才解开,我发现,我真的没什么感觉。无论是在相处中她的温柔,还是她突然来的死亡,心底的那些快乐和悲伤总是刚升起就熄灭了。
可能我真的就是如此冰冷,除了自己外都得不到其他什么东西带来的感情,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在意那些爱我人的欲望,但又莫名在奇怪的地方不停在意。
我躺在床上一直在不停思考,哪怕我觉得已经得到答案了我依旧停不下来,这让我甚至产生了一股错误的眩晕。
然后,一声惨叫和一股怪怪的味道被我让我起床把窗户关上了。
过了会后,我觉得我意识到我正在非常无聊的思维发散,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空洞洞的,最后我想还是该睡一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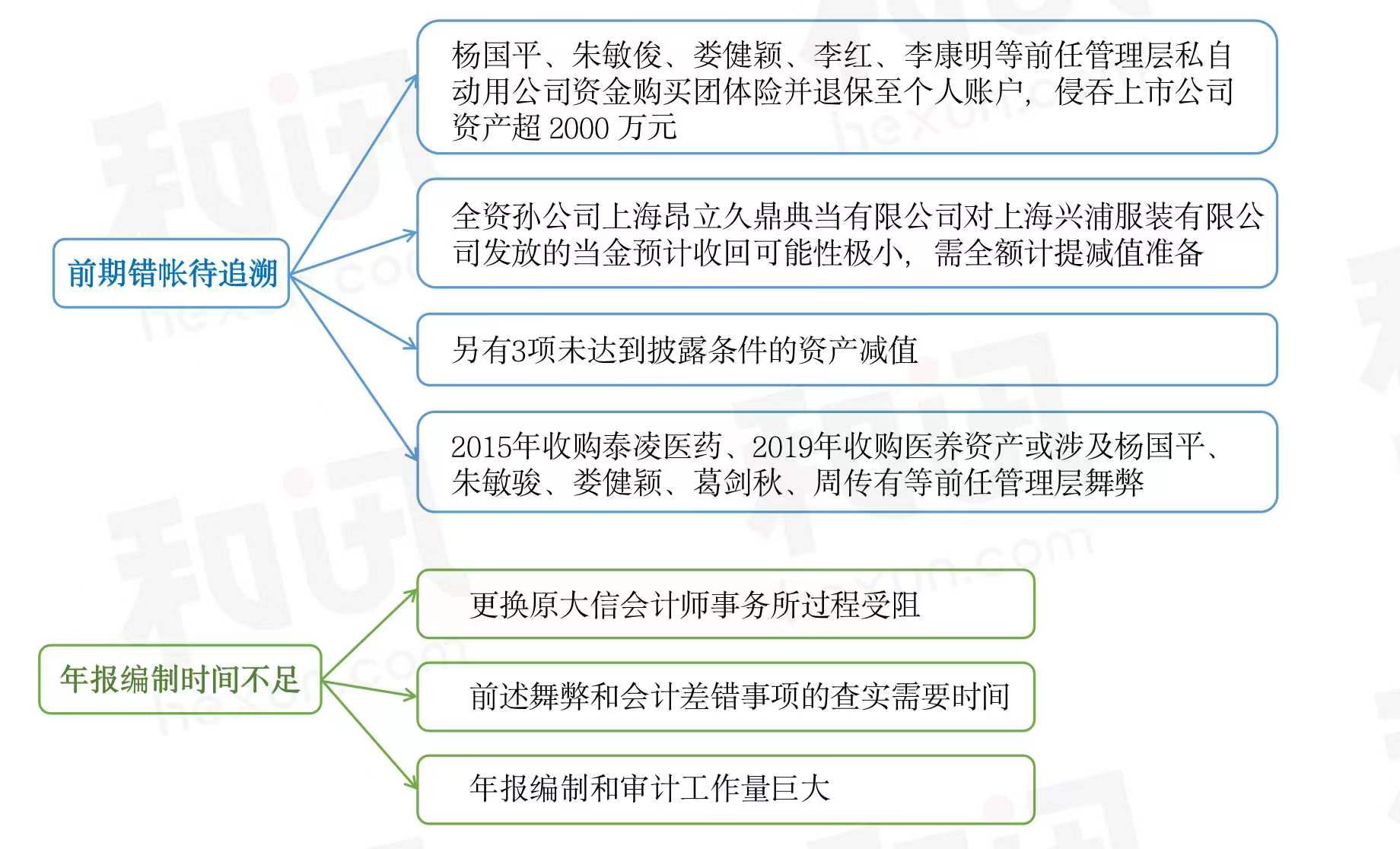

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
营业执照公示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