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晓寒
太阳落下,林子里变得幽暗起来,眼前的事物,像谁用画笔加深了色彩。
天空被纷乱的枝柯切成奇形怪状,中间那一大片照旧灰蓝,只是多了几丝羽毛状的云彩,低低地浮着。天边的云,暗红,沉闷而干燥,被吹成一浪一浪,像被飓风刚刚卷过的红色沙坡。余晖里,远山由青转蓝,线条趋向柔和,一根挨着一根,沿着天际线蜿蜒。最近的那一座,仍旧斑斓多彩,偏暗的色调,像是一幅收藏了多年的国画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山的那一边,月亮理好了装束,蠢蠢欲动。
风比白昼大了,凉了,钻进林子,扑过大大小小的橡树、苦槠、锥栗、栲树、樟树,树下那层厚厚的枯叶发出沙啦沙啦的响声,有些被吹了起来,颤颤悠悠地往前飘,擦着我的身子,穿过树的空隙,落在一蓬长着青苔的藤蔓上,还有几片暂时没有着落,在慌不择路地翻着筋斗。不时有树叶簌簌地落下,大多是橡树和锥栗还未落光的叶子,正面灰黄,背面泛白。橡树的叶子重,落得快,直直地坠;锥栗的叶子长而薄,被风甩来甩去,甩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偶尔会有一片杜英的叶子飘过头顶,不知从哪里来的,形似柳叶,红得炫目,划过一道弧线,无声无息地落到枯叶上,像贴了枚醒目的标签。
秋天刚一到来,风就开始了这项工作,它勾结阳光,一点点把林子抽空。溪水瘦下去,石头裸露,草枯萎,叶子落下来,茂密的森林变得空阔疏朗,像人间的一场繁华,瞬间凋零。据说雪崩是因为一座山积雪太多,无法托载,以致轰然坍塌。一些树木也是这样,不顺从节令落掉叶子,洗尽铅华,回到本源,就有可能落入另一种命运,因为消耗过大而营养不良,形容枯槁,最终走向死亡。大自然是最优秀的哲学家。这就像人生,如不懂得放下,什么都死死地抓在手里,就有可能成为那头被最后一根稻草压死的骆驼。
小溪在一面山坡的脚下,其中的一段紧靠着一条羊肠小道,大概是很久以前,守山人、伐木者、猎人、炭客,还有采药人和放松油的人共同踩出来的。因为长时间无人涉足,只能依稀看出路的痕迹。上面长满了刀把大的油桐,根根直立,覆盖了当年杂乱的脚印。柔软的枝条上,互生的叶子一片片摊开,黄得均匀、纯粹。属于它们的时间不多了,只要再来几场风雨,就将凋落殆尽。告别前的绚丽,流淌着一种触手可及的忧伤。油桐树生长快,繁殖能力强,六七年的样子,就可成林,开花,结果。到时候,这些油桐会开疆拓土,向四面八方高歌猛进,到了深秋,老远就能听到油桐果叭叭砸到地上的声音。
溪流从一大片五节芒里出来,芒草已经枯萎,叶子黄多青少,耷拉下来,像系着一根根褪色的丝绦。芒花早已被风吹散,小小的朵儿都看不到了,穗像用水洗过一样干净,如原来一样高高地举着,聚集在一起,呈浩荡之势,如飘浮的云朵。这是一座森林的旌旗,森林有森林的仪式。溪水像一条雪,丁咚丁咚地唱着歌,蹦蹦跳跳,越过各种颜色的石子,冲积成堆的落叶,长着苔藓的石头,石头上倒伏的石菖蒲,拐一个弯,扎进一大片枫树林里。溪流的上面横着两根脸盆大的枯木,枝条腐烂成了泥土,具体是什么树,已经认不清了。树皮脱落,裹着层黏稠的暗绿色的东西,两簇菌子挣脱稀疏的霉点,带着一圈一圈粉红的花纹,矗立在树干上,像许多重叠的耳朵,在倾听着什么。其中一棵枯木的旁边,躺着一根竹子,碗口那么大,还没腐烂,被风雨淘成了灰白色,我拿棍子敲了几下,听到哒哒的响声。
溪边泥土潮湿,野草密密地长着,水蓼、婆婆丁、艾草、地锦、灯笼草、苦菜、鲤肠、一年蓬,都绿葱葱的,似乎不知道冬天已经到来。在几块磨盘大的石头边上,还看到了几株兰花,一株从叶底冒出三个花苞,有两株已经开了花,洁白的瓣,点着紫色的斑点,花粉还未掉落,看样子是刚开不久,或许就是昨天夜里开的,我凑近去闻,一缕幽香飘来。我喜欢兰花,家里种了不少,一眼就看出这是春兰,因为这个冬天气候暖和,开得早了,看到它们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,像是听到了春天在低低地歌唱。
我选在一棵五眼果树下搭帐篷,一是地势平坦,二是离小溪近,方便取水。我用一把小铲子扒开枯枝和落叶,捡了些干净的松针铺上,再在边上刨出一片空地,方便生火,深山里的冬夜,有了一堆火,就像有了依靠。这棵五眼果树修直,比饭甑还大,黑色的皮凹凸不平,上面点着白斑。还有不少的果子缀在枝条上,有些掉了下来,被鸟啄光了果肉,剩下核和皮,皱皱巴巴的,还有一些,大概被小兽叼进了洞穴里,留作过冬的粮食。我捡起一枚刚掉落的果子,金黄的皮,偏长的椭圆形,样子像细小的戈壁石。这果子我小时候吃过,皮韧,核大,果肉白色,滑腻腻的,酸,甜。它还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,叫鼻涕果。吃的时候得格外小心,没弄好核滑进喉咙里,麻烦就大了。有人曾吃过这个亏,核卡在喉咙里,进不去,出不来,一个劲翻白眼,差点送了命。所以这种果子一般都不生吃,捡回家蒸熟,去核和皮,做成糕点,放在特产店里出售。我把皮剥掉,放进嘴里吮吸,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,先是酸,慢慢有了些甜味儿。
林子里比先前更暗了。一只鹰出现在头顶,它飞得不高,脑袋和身子略微下倾,尾部翘起,绕着圈盘旋,在寻找食物,为了节省体力,不得不随时调整姿势,大部分时间保持滑翔。它把林子睃巡了一遍后,还是没有发现值得俯冲的目标,只好抱着最后一丝希望,在天空移来移去,驮着越来越重的暮色。我的心思有点复杂,希望它找到食物,不再饥肠辘辘,另一边又巴不得它无功而返。一只鹞子从东边飞来,随后又来了两只,像追逐的蝶,使劲地扑打着翅膀,归心似箭的样子,似乎它们那温暖的巢,即将被谁占据。
我已捡了不少柴火,有茶树、桎木、槠树、黄檀,这些木头,拿在手里,暖洋洋的,一敲邦邦响,堆在一起,混杂着干燥的清香。不过,我还是决定再去捡一些,冬夜漫长,以免到时不够烧。穿过几棵粗壮的杜英,一个桎木、藤蔓和野樱桃杂生的山窝,跨过几根斜躺着的腐木,上一个缓坡,出现一个山坳,两侧长着成片的冬茅,看走势是两座山之间的分水岭。坳那边有一片松树林,郁郁葱葱,在这里,整片的松树林很少见。我决定去那里捡些枯死的松枝,松木有油脂,起火快,耐烧,是做柴火的首选。
一路上,斑鸠还在不紧不慢地叫,它已经叫了大半天了,也不觉得疲惫。“咕咕——咕——”节奏是一样的,前两声轻短,后一声突然加大,明显拖长,一个劲往下坠。这声音总让我想起布谷鸟的叫声,听着会产生同一样的感觉,即使挨得再近,就在附近的哪根枝条上,也像离得很远,仿佛隔着一重又一重的风云,极易勾起莫名的惆怅。
斑鸠的叫声没停下,竹鸡开始叫了,声音从山丘里传来,又脆又亮,六七声连在一起,中间没有停歇,“地主婆,地主婆,地主婆……”因为叫声的缘故,很多地方就直接称它们为地主婆。我一边在拖一根枯死的松枝,一边细细地听,有三只,轮番地叫。这种鸟我见得多,很漂亮,背部灰色,腹部红黄夹杂,在鸟类当中,个头算是大的,每只有五六两重,三五只一群。它们白天忙着觅食,只有到了傍晚,才会叫。也不是每天都叫,得看天气。山里人说,竹鸡叫,第二天准是个大晴天。这让我十分高兴,我并不希望在这深山老林里遭遇阴雨天气。
竹鸡叫了一阵,找到了栖息的树枝,不再叫了,准备安度夜晚。林子里恢复了寂静,只听到风吹过树梢呼呼的声音。不知什么时候,天边的红云消失了,变成灰蒙蒙一片。
正在我凝神的时候,后面山上传来扑喇喇拍打翅膀的声音,野鸡开始上树栖息了,它们一只接一只,飞向自己中意的枝条,将在那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,要等到黎明到来,太阳照暖这片林子,才会飞下树来,继续寻找食物。野鸡喜欢群居,一群少的有十几只,多的有三十几只,它们不像竹鸡一样警惕,害怕外界的打扰。白天穿过这片林子的时候,就看到了两群,一群一边觅食,一边“咯咯咯”地叫着,另一群在溪边喝水,领头的那只公鸡,个大,估摸着有五六斤,通身白色,尾巴上的羽毛高高扬起,像一个威风的将军。它们看到我,仍是不慌不忙,直到我走近,才叫几声,一齐飞了起来,消失在对面的山上。
安静片刻后,响起了啄木鸟敲击木头的声音,“笃——笃——笃——”慢腾腾地,节奏感很强,像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伐木声,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腰缠手巾的伐木人,双手握着斧子,落下,举起,举起,又落下,木屑像雪片一样飞。隐隐约约的声音,有《诗经》里的原始、粗犷,夹着混沌、苍凉,林子似乎一下子更加寥廓了。
松枝上缠着藤条,费了好一阵劲才拽脱。我搂着几根松枝往回走,看到一只松鼠沿着一棵栲树往上爬,嘴里叼着一颗锥栗。可能是突然看到我这个陌生的闯入者,两只黑豆般的眼睛嘀溜溜地转,眼神里充满了孩子般的狡黠和好奇。很快,它收回目光,“吱”的一声,不知蹿到哪里去了。
林子里活跃着很多动物,还有一些我没有看到,像常见的竹鼠、黄鼠狼、豪猪、穿山甲,不知躲在什么地方,或许它们看到了我,只是我不知道。有些是习惯夜间活动的,还没出来,比如野兔、麂子、野猪、果子狸、獾子、野猫,豹子也还是有的,只是数量不多,很难见到。几十年前,这些林子里还有老虎、豺狼和麋鹿,现在已经绝迹了。
对于动物们来说,现在是最好的季节,霜雪还未降临,这又是个暖冬,林子里仍旧保持着秋天的样子,它们不用为如何对付寒冷而发愁,更不用担心找不到吃的。无边的森林,是一座天然的粮仓,橡子、锥栗、苦槠、栲树的果实,这些坚果,已经掉到了地上,可以任意享用。还有很多浆果,野葡萄、猕猴桃、山茱萸、酸枣、君迁子、野蓝莓、金樱子,都是难得的美味。动物和树木之间的关系,极其简单,不分谁是主宰,谁是附庸,谁养活了谁,谁该回报谁。动物们把果子吃下去,让自己不至于挨饿,然后将其中一部分种子带到另一个地方,让它们发芽、生长、开花、结果,等到若干年后,有更多的果子来喂养它们。彼此互相成就,各不亏欠,逐渐成为一种秩序。这种森林里的秩序,包含着信任、爱与宽容,从远古延续到今天,从未改变。只是这种美好的秩序一旦离开森林,搬到烟火人间,就会不断遭到扭曲,最后变得面目全非,成为另一种秩序。
回到五眼果树下的时候,小溪上泛起了轻烟,一缕一缕,漫过粗壮的树木和垂下的枝丫,向着我的帐篷飘来,像时隔多年前来造访的故人。一会儿工夫,小溪看不见了,帐篷的一角也浸染在薄烟中。林子里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,像是一个制造悬念的镜头,里面隐藏着神的故乡。
天完全黑了,夜色覆盖了林子。
月亮越过山头,出现在天边。山里的月亮,胖嘟嘟的,像捂在坛子里刚发酵过。洁白的光如一匹丝绸垂了下来,我听到了月光拍打树枝的声音,然后被枝丫划破,碎成光点,叮叮当当地落下。夜太黑了,风已经分不清方向,赶着它们满地跑,仿佛那条灿烂的星河跌落到了地上,光芒闪烁的河水一会儿涌向那头,一会儿又“哗”的一声倒过来,向着这头飞奔而来。
星星出来了,刚开始是稀疏的几粒,看上去那么遥远、晦暗、懒洋洋的,半天才动一下。随后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,渐渐开始下坠,越来越近,直到贴在对面的山顶,卡在头顶的树枝上,硕大的一粒,每一粒都像有人刚刚用心地擦过,迸溅出蓝色的光芒。
这时候的林子,像是童话里的背景。
我点燃火堆下的松针,火苗蹦出来,使出浑身解数钻过杂乱架着的木头的缝隙,一会便伸直了腰,成了一座逶迤的火山。干燥的硬木在火堆里噼里啪啦地响着,火星不断跃出,胡乱地飞动,很快就毫无征兆地消失了,另一些火星又蹦出来,填满了这个空隙。火光驱散了夜色,形成一个圆形的光圈,笼罩了我和我的帐篷。有两只蛾子飞了过来,像是两个顽皮又兴奋的孩子,围着火堆转了几圈,然后在火苗上方飞过来飞过去,似乎在做一个永不厌倦的游戏。蛾子逐光而来,随时准备着为光而献身,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里,它们已经找不到这样的火光了。而我,更愿意相信,它们是为这堆火的温度而来,将在这个深山里的冬夜,享受一堆篝火给予它们的温暖。
风仍在吹,林涛不疾不徐,像在为大地哼着一支抒情的歌曲。
这个夜晚,我将在这片深林里独自安睡,自从封山禁猎以后,这些林子里再也见不到人影。这里,属于罗宵山脉的一部分,往东走,几百里都是莽莽苍苍的森林。相对于大地来说,这条山脉太小了,在地图上看,只是一根不起眼的曲线,而于我而言,却是如此的浩瀚苍茫。不过我并未感到我独自占有这片看不到边际的林子的喜悦,我从未产生过这样奢侈的想法,人活在这世上,以占有为乐,总想多占一点什么,实际上谁也不可能占有那么多,从生到死,属于自己的,就只有三尺黄土。
我就着火光吃了一个面包,喝了点刚烧开的热水,钻进帐篷,准备睡去。想起我计划进入森林的头一天,家里人和朋友一再劝我,语气郑重,类似于告诫:你得邀两个伴去,山里危险,怕出意外,再说,夜里也容易孤独。我婉言谢绝了,就是去山里走走,哪来的危险和孤独?相反,我生活了几十年早出晚归的那个地方,经常让我感到孤独,到处布满了看不见的陷阱,可是,从未有人来安慰过我,更没有人向我提出过警告。
我躺下,望着月亮和枝条上的星星,听林涛,流水潺潺,猫头鹰叫,火星三三两两地爆裂,感到这个夜晚的美好。天地敞开,有那么多树木那么多鸟兽相伴,它们就是我的邻居,这一大片森林,归我们共同拥有,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睡着,各做各的梦,我将在梦里,等待明天的第一缕阳光落到脸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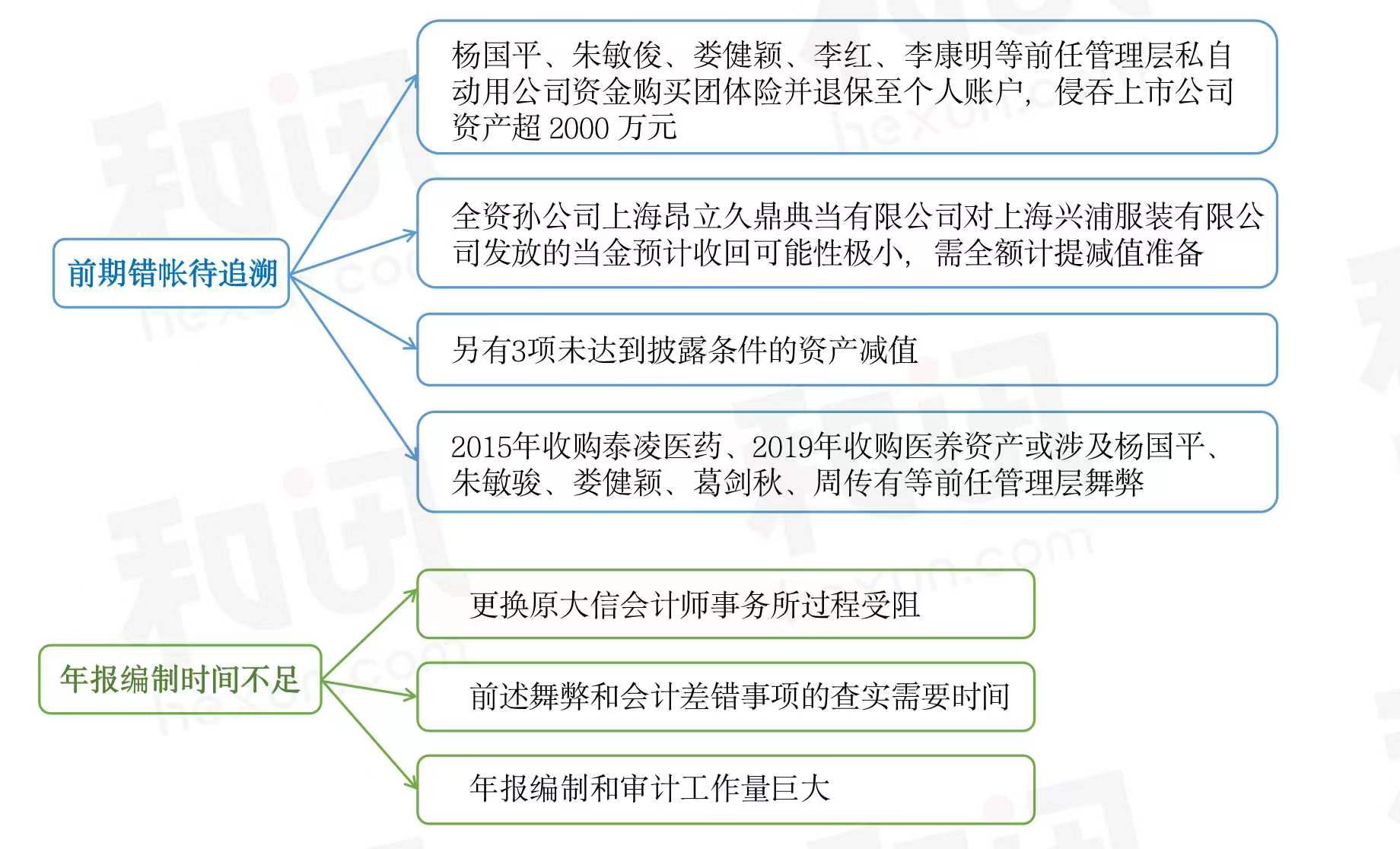

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
营业执照公示信息